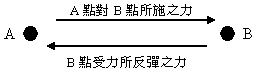
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以考古學所進行的歷史研究,存在著論述與非論述領域無法溝通的問題。除了《古典時代瘋狂史》之外,從《臨床醫學的誕生》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一直到《知識考古學》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傅柯似乎都無意處理這個問題。在結構主義的影響下,傅柯整個研究偏向於語言結構的分析,因而使他的歷史分析專注於論述層面,從而破壞了原本他在瘋狂史中所建立的論述與非論述彼此互動的歷史形式。系譜學的出現,為考古學所存在的方法論問題開啟了一道曙光,藉由分析「力」的場域,傅柯開始尋找那些使論述變動的來源,並因此而將歷史研究的範圍重新擴大到非論述的層面。一旦傅柯將系譜學運用到歷史研究上,他所搜尋的主題將不再局限於知識論述層面,傅柯開始尋找與權力相關的課題,由此而開啟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歷史領域:監獄與性意識 (sexuality) 。
本文所涵蓋的時間是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從傅柯成立「監獄信息小組」 (GIP,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開始,一直到《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與《性意識史》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分別出版為止。由於本文將斷限止於一九七六年,是否意味著本文將棄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這段傅柯最後的時期於不顧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九七六年,傅柯發表《性意識史》,宣佈他將開始進行一長達六卷的性史研究,《性意識史》是這一系列作品的導論也是第一冊。此後,傅柯有八年的時間未曾出版任何作品。最後終於在一九八四年出版了性史第二冊《愉悅的享用》 (The Use of Pleasure) 與第三冊《自我的關切》 (The Care of the Self) ,但就在這兩本書出版的幾個禮拜後,傅柯因病去世。由此看來,本文若要將傅柯的作品依年代順序分別進行分析,則應該將性史第二冊與第三冊列入討論的內容,然而之所以不這麼作的理由有兩點。
首先,《性意識史》本身的內容就已經包涵了《愉悅的享用》與《自我的關切》,因此可以只將討論集中在《性意識史》上。傅柯一開始進行性史研究時,並沒有想過要分成數卷,但是後來他發現他所面對的內容相當繁雜,因此不得已才將性史分成六冊。而後為了避免讀者將這些書彼此割裂來閱讀,忘卻了它們原是一個整體,因此他先出版了《性意識史》,作為整個性史研究計畫的總論。傅柯生前只完成了三冊性史,在另外三冊沒有完成的狀況下,單憑分析《愉悅的享用》與《自我的關切》,並不足以瞭解傅柯的構想。也許這時我們應該回歸到《性意識史》,或許才是掌握傅柯性史整體性的較佳作法。
其次,《愉悅的享用》與《自我的關切》與其說是歷史作品,不如說是哲學性的作品。這是因為這兩本書在討論希臘、羅馬思想家的作品時,不只是忽略了歷史脈絡,甚至在作品與文本的挑選上都相當任意。1 面對傅柯這些不尋常的作法,我們與其責怪他在進行歷史研究時舉證輕忽與漫不經心,不如說傅柯有意在此樹立他個人獨有的哲學思維,也就是說,這兩本書並不是歷史作品,而是他個人哲學思想的展現。因此,本文將不對這兩本書進行個別分析,而將其併入《性意識史》之下來進行討論。
《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乃是傅柯將其系譜學具體運用於實際歷史研究的明證,同時也是傅柯從一九六九年以來對政治活動與權力運作的關注所產生的思想結晶。相較於之前的考古學作品,傅柯這個時期的研究無疑具有濃厚的批判性與實踐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傅柯此期也廣泛參與了改革獄政以及聲援國外異議人士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多半是透過與毛派份子結盟來完成的。毛派是西方知識份子吸取毛澤東的理念而形成的左派派別,主張一切由人民決定而非由政府官僚或其他特定團體來決定;毛派認為藉此可以弭平一切階級的差異,而建立真正的民主。傅柯在參與改革獄政的過程中,曾激烈地主張廢除所有的警察機構及法院,而由人民決定社會公敵,並由人民來予以公審及處罰,完全一幅毛派的作風。2 姑且不論毛澤東想法的對錯,我們都必須要知道一件事:西方知識份子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沿用確實帶有一些浪漫情懷,同時也有極大的誤解,而這種誤解來自於西方知識份子對於反體制力量的渴求。現代福利國家的興起與產業的急速分化,一方面使工人的工作環境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工人」已變成內容多樣的職業,這使得左派無法組織龐大而團結的工人來對抗政府,但是改革的需要仍然迫切,於是毛澤東在中國掀起的土地改革(一九五0)年代與「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遂提供了西方知識份子某種改革社會的靈感與力量(雖然是全然是一種誤解):不再限於工人,而是讓全體民眾站起來,取代政府,自己決定一切。而這群受毛澤東「感召」的西方知識份子便被稱為「毛派份子」 (Maoist) 。
一九七一年,一群毛派份子計劃要對法國的獄政問題發動抗爭,他們希望能邀請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參與,以壯聲勢。傅柯於凡辛大學的表現,早已引起他們的注意,如今傅柯又在一九七0年成為法蘭西學院的教授,因此,這些毛派份子便企圖邀請傅柯參加。最後,他們不僅得到傅柯的同意,而且在他的協助下成立了「監獄信息小組」。「監獄信息小組」主要的工作在於訪問獄中的犯人,藉由他們的嘴來吐露獄中悲慘的實況,然後再利用媒體的傳布來喚起大眾對獄政問題的關注。巧合的是,這個小組成立不久,法國各地監獄便接二連三地發生暴動,大眾媒體對此的廣泛報導,使得「監獄信息小組」利用這個機會讓獄中訪談傳布到法國每一個角落。然而隨著「監獄信息小組」的成功,傅柯也與這個小組漸行漸遠,因為它已脫離傅柯原先所構想的原則。傅柯認為,沒有人有權利代替犯人說話,無論犯人的處境如何,小組的地位只是以犯人為主,要以作為犯人的傳聲筒自期,而不是幫犯人作主;然而隨著小組的擴大,組織開始反客為主地為犯人爭取權益。在傅柯眼裡,這只是一種偽善,看起來是打著援助的旗號,事實上卻是堵住犯人的嘴,自以為是地為犯人作主,這種作法與那些成立監獄的統治機構也沒什麼兩樣。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後,傅柯離開了小組。3
傅柯在揭露獄政的同時,也一邊進行他的學術工作。傅柯一方面著眼於當下的監獄體制,另一方面也從歷史方面去尋找監獄的形成過程。一九七三年,傅柯與一群學者將十九世紀一個有名案例的檔案整理出版,書名為《我,皮耶‧里維耶,殘殺了我的母親、妹妹與弟弟》 (I, Piere Riviere, having slaughtered my mother, my sister, and my brother) 。里維耶於一八三五年的六月三日,在諾曼第的家中殺死了他的母親、十八歲的妹妹與八歲的弟弟。傅柯藉由里維耶當初留下的回憶錄,說明了醫學論述、法律權威與警察系統彼此鬥爭以搶奪權力的過程,發現它們都在爭取以自身的論述作為決定犯人最後結局的最高標準,霎時間一個兇殘的殺人事件變成了論述間的權力鬥爭場,每個論述都在爭奪處置犯人身體與心靈的權力。4 這本書開啟了傅柯從權力角度觀看歷史的一頁,傅柯在一九七五年完成《規訓與懲罰》便是以這本書的分析為基礎,加以擴大寫成的。
《規訓與懲罰》出版後一年,傅柯完成《性意識史》。相對於監獄,性意識似乎與權力沒什麼關係,同時也與傅柯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格格不入。也許傅柯未曾將性意識排上他的街頭抗爭議程,然而他卻每週都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廳中,向他的兩、三百位聽眾說明研究性意識的重要。傅柯認為,在當代社會的權力─知識關係中,性意識正佔領著核心的位置,所以研究性意識乃是瞭解權力─知識關係的關鍵。5 監獄與性意識因此在傅柯的權力研究中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們是傅柯藉以分析現代社會權力與知識關係的兩條並行主題。
本章處理傅柯最後一個時期的思想,將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討論。首先,本章將說明《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所呈現的新歷史寫法。傅柯為了研究權力而從尼采那裡借用了系譜學方法,以這種方法所寫成的歷史,打破了以往考古學深陷於論述層面的局限,而能合論述與非論述為一整體,構成了新的歷史寫法。其次,本章將評論系譜學所構成的歷史形式。傅柯運用系譜學所呈現的歷史,看似回歸到《古典時代瘋狂史》論述與非論述彼此結合的方式,然而並不完全。由於繼承尼采的觀點,傅柯的系譜學所呈現的歷史形式隱隱帶有反歷史的傾向;另一方面,傅柯原本想藉由研究權力來針砭現代社會的想法,也因尼采權力觀的隱含設定而解消。
《規訓與懲罰》的副標題是「監獄的誕生」,與之前的著作相同,傅柯之所以選擇監獄作為他考察的中心,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顛覆傳統歷史論述在監獄制度上所持的正面看法。傅柯之前的歷史作品,不斷挑戰著傳統歷史論述所認定的人類歷史是一個越來越人道與越來越進步的進程;而面對監獄的歷史,傅柯同樣要證明,監獄的產生與人道、進步沒有關係,相反地,監獄只是另一種權力形式,而且是另一種更徹底的權力技術 (technology of power) 展現場地。
監獄制度的產生一般被視為是對罪犯的一種「人道」表現。如果閱讀《規訓與懲罰》開頭所描述的一七五七年一場肢解弒君者達米安 (Damien) 的殘酷場景,一直到一八三七年佛榭 (Leon Faucher) 所設計的巴黎少年教養院所呈現的安寧、恬靜與秩序,讀者不得不產生一種印象,那就是從十八世紀(古典時代)到十九世紀(現代),人們在對待罪犯上的確更加的人道與更加的「文明」。6 然而這只是傅柯故意塑造的假象,他隨後就將戳破這個神話。
傅柯認為,傳統歷史論述之所以會將監獄的產生視為一種人道的象徵,是由於這些論述只從法律與政府理論的層面來考量這個過程。達米安因意圖弒君而招致兇殘的肢解之刑,這對於傳統歷史論述來說,有兩種意義。第一,達米安面對的是「朕即國家」 (Etat est moi.) 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法律是君王意志的體現,違逆法律等於違逆君王的意志。達米安的犯行,不僅是違逆了君王的抽象意志,而且還訴諸於實際對君王身體的觸碰──弒君。因此達米安所犯的罪乃超乎以往,須配以極刑。第二,處決的過程之所以要公開,在於重新宣揚君王的權力。以殘酷的手法對待達米安,意味著達米安將以自己所受的痛苦來修補他對君王權力所作的侵犯,而讓所有民眾觀看他的哀嚎與懺悔,更可確認此一修補的過程。7
在舊王朝時代,觸犯法律等於觸犯君王的意志與權力,之後的處分則是為了修補君王的權力,無論是訴諸於身體的傷害或凌虐致死,都得在公開的場合下進行。這種狀況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改觀。大革命以後的政府權力,來自於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 ,因此,觸犯法律等於觸犯了社會全體 (social body) 的意志與權力,罪犯因此將成為社會公敵。8 對於公敵的懲罰,並不像舊王朝時代那樣訴諸於身體的疼痛與生命的奪取,而是以大革命之後所樹立的人權觀念為基準。在這個時期,人的自由被普遍地看重,因此奪取人的自由遂成為懲罰的最佳方式。設立監獄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拘禁犯人來剝奪他的自由。從公開處決轉變成拘禁,之所以能說這個過程漸趨人道,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是因為政府的權力來源由君權神授變成社會契約,人民不再只是臣民,而可以藉由代議的方式組成政府;權力由下而上,避免了特權階級與不平等。同時,在懲罰罪犯上面,不再有野蠻的流血場面,同時也不再有君王的任意懲戒,而是從社會全體的利益來思考罪犯罪行的大小,進而決定懲罰的強度,即便要懲罰也訴諸於剝奪犯人的基本權利。9 這個懲罰方式的演變,從以一人利益為考量到以社會全體利益為考量,從任意懲戒到依據罪行訂定罰則,正符合了平等與理性,另一方面則又避免了殘殺,也合乎人道。
這段罪犯懲戒史之所以看來日趨人道,在於它基於一個設定,認為基於社會契約論所構建的政府,遠較基於君權神授而形成的政府在法律上更能保障社會利益與天賦人權,而當前者為了保障社會利益與天賦人權而不得不對犯法的人作出懲罰時,它的作法也較為溫和。然而傅柯認為,從權力技術運作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所顯現的其實是權力技術愈趨完善的過程,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政府實際上並不是為了保障社會利益與天賦人權而存在,它所進行的是新形式的權力運作,也許在運作手法上不像舊王朝那樣明目張膽,但卻更為全面而徹底。也就是說,現代政府所發展的支配體制,反而比舊王朝時代更為周密而完善,它並不是要保障個人自由,而是要更充分地利用它所擁有的人力資源。所以,如果只從法律條文與政府組成方式來衡量這段歷史的話,只能看到形式上的人道,卻完全看不到抬面下實際發生的支配體系,傅柯的權力分析則試圖彌補這一點,並進而推翻前者所創造的人道神話。
傅柯進行權力分析時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我們在第四章曾提過的系譜學。系譜學是傅柯為了補充考古學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它的主要任務便是研究權力。然而,系譜學之所以特殊,來自於它所處理的「權力」與一般的權力不同。我們可以引用傅柯自己對「權力」一詞的定義來說明:
我所說的權力既不是只在確定的一個國家裡保證公民服從的一系列機構與機器,即「政權」,也不是指某種非暴力的、表現為規章制度的約束方式;也不是指由某一分子或團體對另一分子或團體實行的一般統治體系,其作用透過不斷地分流穿透整個社會機體。用權力的概念研究權力不應該將國家主權、法律形式或統治的同一性設為原始論據;確切地說,它們不過是權力的最終形式。對我來說,首先應該將權力理解為眾多的力的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它們發生作用的那個領域,而這個領域也構成了這些力的組織……權力無所不在……在任意兩點的關係中都會產生權力……權力不是什麼制度,不是什麼結構,不是一些人擁有的什麼勢力,而是人們賦予某一個社會中,複雜戰略形勢的名稱。10
據此,權力並不是一個具體之物,而是一個抽象的力,它在任意兩點間發生。無數的點就產生無數的力的交互關係,也就是權力關係。所以,系譜學所研究的是其實是一個抽象的力場 (field of force) ,而非具體的制度或論述。
傅柯對權力的定義,其實完全承自尼采。事實上他的系譜學也是來自他對尼采思想的解讀,然而這並不表示傅柯原封不動地移植了尼采的想法。在解讀尼采的過程中,傅柯已用自己的理解將系譜學的概念作了轉化,而讓系譜學獲得了新的意義。若比較尼采與傅柯在系譜學上所持的觀點,從同的方面來說,兩人同樣都討論「力」的問題,傅柯接受尼采將權力關係定義為眾多抽象的「力」的關係;從異的方面來說,尼采偏重於力的「破壞」面與否定面,而傅柯則強調力的「生產」面與積極面。
從〈尼采、系譜學、歷史〉中可以看到,尼采的系譜學強調「力」彼此鬥爭的過程。尼采將「力」定義為暴力,認為較強的力能將較弱的力所樹立的規則與秩序全都掃除殆盡,從而樹立自己的規則與秩序。如果按照尼采的看法,那麼事物的變化總是以衝突與鬥爭為形式來展現,所以新歷史作品的出現必以破壞舊歷史作品為代價,而對於文本的再詮釋必以對舊詮釋的不滿與拋棄為前提。傅柯起初也同尼采一般主張力的破壞面與否定面,然而後來卻改變態度。在一九七七年的訪談中,傅柯曾說明這個轉折來自於他在一九七一、七二年間參與「監獄信息小組」的經驗。在此之前,他認為權力的效果總表現在排除與否定,也就是說,忠於尼采的看法,因此無論在〈論語言〉或〈尼采、系譜學、歷史〉,傅柯並沒有太多自己的創見。然而參加小組之後,他的想法改變,認為權力所具有的性質並不是破壞,而是生產,並因此而寫了《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11 「權力生產知識」這句話也是在這個思想脈絡下產生的。12
綜合以上,傅柯的系譜學的研究對象,乃是一抽象的力場,在這力場中,任何一點所發出碰撞另一點的力,看似要破壞對方,其實在碰撞中,會有所生產。然而生產什麼?或怎麼生產?就要從傅柯的實際分析中來判斷了。
路易十五( Louis XV, 於 1715-1774 在位)對意圖行刺他的兇嫌達米安所施加的酷刑,在傅柯眼中,象徵兩點之間「力」的作用。當兩點之間有力的作用時,某一點施力於另一點,另一點並不僅僅是受力而已,而且還會產生抵抗作用,也就是會將力量反彈回去。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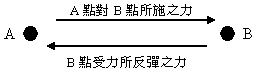
傅柯用這種觀念來解釋達米安的狀況。路易十五在此象徵 A 點,而達米安則是 B 點,當路易十五對達米安施以酷刑時,表示他對達米安施以某種力(權力),然而達米安看似被動地遭受摧殘,但事實上他也回報路易十五某種力(權力)。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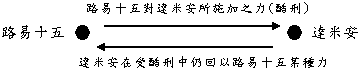
我們可以理解路易十五對達米安所施加的力是什麼,因為它以明顯的酷刑形式表現;但是達米安的身體在遭受肢解時能對路易十五作出什麼反饋呢?這一點就必須要帶入傅柯權力可以生產而非破壞的觀念,才能解釋。
傅柯認為,公開處決的儀式具有修補君王權力的功能,這個想法與傳統歷史論述並無不同。然而如果再搭配傅柯的權力概念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當路易十五對達米安施加某種力(酷刑)時,藉由公開的儀式,在觀看的群眾間形成了對君王權力的感知與談論,因而產生了對君權的論述。也就是說,當路易十五施力於達米安的同時,產生了君權論述,這就是所謂的權力產生知識。另一方面,達米安被凌辱的身體又是如何產生抵抗的力量,反回去作用在君王身上呢?在公開處決的儀式中,群眾除了從恐怖場景中看到令人畏懼的無上君權,也產生了複雜的情緒,不管是集體鼓譟起來叫好或辱罵,或者是不滿處決過程或藉著人多乘機鬧事,都嚴重傷害到君權的莊嚴。13 也就是說,藉由觀看達米安的身體,群眾產生多重論述,不管是英雄論述、弒君論述等等,都直接干擾了君權的完整,於是一場修補君權的儀式很可能弄巧成拙。達米安的身體反過來對君權施加了力,並因此產生了一連串傷害君權的論述。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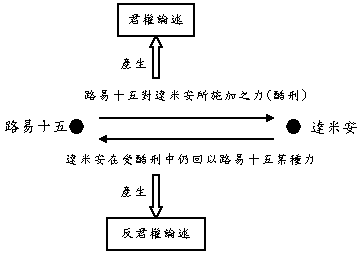
所以,古典時代的無上君權,在往它的臣民伸展權力的同時,也遭到同等力道的反擊。相反於傳統歷史論述所呈現的全方位掌控臣民的現象,傅柯認為,古典時代的君權必須時時刻刻戒慎恐懼,一方面不能錯過確認君權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又擔心群眾中所產生的反響。
這樣的權力運作機制顯然不穩定而且危險,古典時代末期的有識之士早已有見於此:「在舊王朝的最後幾年……審判時,對待窮人更加嚴厲,無視證據就加以定罪,導致上下離心,彼此懷疑、敵視與畏懼。」14 他們開始呼籲在司法上作適當的改革,然而不久大革命爆發,古典時代結束。
按照傳統歷史論述,大革命後的政府以社會契約論為依歸,保障全體社會利益與天賦人權,然而傅柯反對這種說法。傅柯認為,古典時代要求司法改革的呼聲,延續到革命後的制憲會議,然而改革的目標不是以保障人權或人道為考量,而是賡續古典時代末期對權力運作機制的討論,企圖建立一套更完美的權力系統。改革者認為舊系統之所以不穩定是因為中央的權力過大。以君王的肉身之軀作為權力中心,使得權力的運作不能均勻、持續而綿密地作用在臣民身上;另一方面,手攬大權的君王因為過於醒目,容易變成眾矢之的,而成為民眾反對的目標。新的權力機制因此應該避免使權力過度集中,並且要讓人看不見權力的來源;這樣才能一方面有效率地施力,另一方面卻又使反抗力找不到反擊的目標。15 所以,從古典時代到現代,並不存在一個越來越人道的懲罰方式,而是要求懲罰地有效率並且不帶任何反效果。
要建立一個全新而運作良好的權力機制,需要有一套新的權力技術,才能滿足改革者所期望的條件:均勻而不間斷地施力卻又不會有反作用力。傅柯發現,這一套新的權力技術其實在古典時代就已經存在,但並沒有被整合為古典時代權力機制的一部分。這套權力技術由兩種機制構成,一是監獄制度,一是規訓機制。
監獄制度在古典時代的功能在於「把人當做抵押品來扣留」。16 無力償債或者無法服勞役者,可以用監禁來抵償。從法律上來看,關在監獄裡面的人並不是犯人,他們只是採取不同的方式來還債或是服役。古典時代末期,法國由於農作歉收,加上對外戰爭頻仍,使得社會上的游惰著日漸增加。這些游惰者一方面無法繳稅,一方面逃避勞役,因此必須按理要接受監禁;然而另一方面,這些游民數量龐大,有時會觸法犯罪,擾亂社會秩序。在這種狀況下,原本用來扣留人以為抵押的監獄,突然關滿了無法納稅的游民,而其中也夾雜了不少犯法人士。就在這不分青紅皂白共處一室的狀況下,監獄在古典時代末期開始容納犯罪者,並因而形成一種懲戒性機構。17 按照傅柯的分析,監獄制度早在古典時代就已形成一種懲罰機構,並不是在大革命之後才出現,傳統歷史論述的看法因而是錯誤的。
光是監獄制度本身還不足以構成現代權力機制,更重要的是要搭配上規訓機制。傅柯將規訓定義為一種「規定某種對人體的具體的政治干預模式,一種新的權力的微觀物理學 (micro-physics) ……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18 這種政治解剖學以人體為對象,細密地將人體分割為各部分,將每一部分視為政治權力的施力對象,以便得到最大的使用功率。傅柯認為,這種政治干預模式始於古典時代初期,也就是十七世紀,出現的地點原本是在修院,然後逐步擴展到學校、工廠、醫院,最後傳到了軍營裡面。19
規訓作為一種人體細節的政治干預模式,它的運作可以分成兩個角度。從肉體(被規訓者)的角度來看,規訓從肉體中創造出四種個性。首先是空間性,從空間分配中打斷每個人的聯繫,使混亂的場面單純化,而能單獨地針對每個人進行考核;第二是有機性,將人體的動作分解成細節,並在每個細節上反複練習,所有的人必須以矯正過後的姿勢來進行每一個分解動作,務使人體活動能達到最有效率的境界;第三是創生性,將人體要學習的活動或計劃分割成一系列的步驟,循序漸進,並在每一步驟的末尾加以考核;第四是組合性,要求熟練於以上各種活動的肉體,以一氣呵成的方式進行演練 (maneuver) 。20
另外,從規訓者的角度來看,則可分為三個層面。首先是層級監視,在被規訓者當中選出一些人,作為被規訓者當中的監視者,以提高整個權力機制的效能;其次是規範化裁決,規定統一的標準,能合乎標準的就獎賞,不能的就懲罰;最後則是考試,結合了層級監視與規範化裁決,考試除了能對後者進行測試並進行賞罰,考試試卷還可以作為文書檔案,當作前者的參考文件。21
監獄制度與規訓機制結合而成的一套權力技術,構成了現代權力機制的基礎。而藉由這一套權力技術所造就的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的全景敞視建築 (panopticon) 。全景敞視建築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樓。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只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就可以監視所有牢房內的犯人,而犯人卻看不到塔中的人。22 這種建築形式無疑是監獄制度與規訓機制結合的具體表現。藉由全景敞視建築,監獄管理人可以在中央塔輕鬆地對每個單獨被囚禁的犯人進行監視,他可以命令他們進行一連串的動作,並且在同時間對他們進行評比與考核。另一方面,由於犯人看不到塔中的人,因此他無法確定他是否被監視,這使得犯人完全籠罩在規訓機制的陰影中,一刻不得放鬆。也就是說,在全景敞視建築中,權力可以持續不斷地對某一點施力,然而受力點卻無法確知力的來源來自何處。這正滿足了現代改革者對新權力機制的要求:能不斷地施力又能避開反作用力。
全景敞視建築所展現的權力機制原本局限在學校、工廠、醫院與軍營,然而從十九世紀初開始,逐漸往社會各層面散佈。這個擴展的過程產生了三個現象。首先,現代權力機制對整個社會進行規訓,將社會上所有的人力資源作切實而有效的運用,因此,權力所造成的功效不是壓迫,而是生產。其次,隨著社會逐步地規訓化,整個社會越來越像是一個大型的全景敞視建築,雖然這個建築當中並沒有中央塔,然而藉由權力中心分化成學校、工廠、醫院、軍營及其他社會機構,無數的權力點遂在社會上星羅棋布地散佈開來;受力者所受的力不再像古典時代那樣只來自君王一人,而是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範疇的力,這些力不訴諸血淋淋的暴力,而是以零碎但又帶著堅決的持續,無聲無息地滲透到人的身體與心靈;沒有明顯的權力來源加上令人難以察覺的細微施力過程,受力者所能反饋的反作用力陷於迷惘而無力,促使權力更能無所忌憚地施為。第三,權力中心雖然已被分化成無數權力點,卻不代表權力中心不存在,它只是默默地在各權力點背後支持著權力點的運作;而其支撐各權力點運作的方式就是設立警察機構,以警察來遂行各規訓機制的運轉,所以這個隱藏的中心其實就是國家。23
按照傅柯對現代權力機制的分析,我們可以將其比對古典權力機制,以圖對照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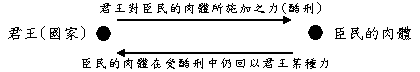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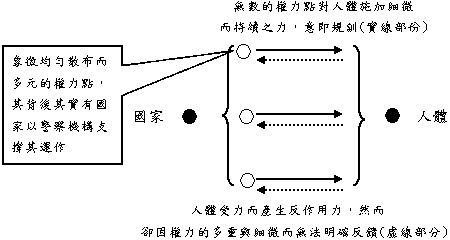
由古典時代到現代,改革者一直盼望著權力運作能日趨穩定而且安全,如今終於實現了。國家隱退到學校、工廠、醫院、軍營及其他社會機構之後,以警察機關協助這些權力點貫徹其規訓機制,而被規訓的人們同時受到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規訓力量,難以反應也無從反應;古典時代的權力來源過度明顯,這個缺失在現代權力機制中不復存在,血淋淋而暴力的權力運作方式也消失了,現代權力機制因此是一個溫柔卻又狡猾的權力場域──它無聲無息地施力且不受報復。然而,現代權力機制仍隱約存在著一個問題,由於受力者仍會產生反作用力,只是一時間找不到反饋的對象,這一股力量若是不加以消除,難保有一天不回撲權力來源。因此,如果要使現代權力機制更加完美,就必須消除這個潛在的危險,而這個重責,必須交給監獄制度來完成。
現代監獄採用了全景敞視主義 (Panopticism) ,運用中央塔來管束犯人。監獄的效能不只局限在監禁,還在於規訓。如果從規訓的角度來看,監獄制度試圖要教育犯人、改造犯人,導正其偏差的行為,而能重新進入社會,然而傅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監獄制度非但沒有起到減少犯罪的作用,反而成為培養罪犯的地方。24 「監獄使培養罪犯的環境成為可能,甚至有鼓勵其出現的意思。罪犯在監獄中彼此忠誠、排定輩份,並且隨時準備支援及教唆未來的犯罪行動。」25 另一方面,獲釋犯人即便要改過自新也不可能,因為他們留有案底,社會並不接納他們,同時警察也盯緊這些人,隨時準備發現他們的小錯,抓他們入獄。26
監獄制度因此成為培養累犯的地方。假設一個人初次犯罪,在判刑後被送入監獄,他首先要面對監獄內的罪犯社會,而在出獄之後,他的案底馬上讓他成為被社會排斥與被警察監視的對象。這樣的人在社會找不到工作,而且永遠都被懷疑是可能為惡的人,在這種狀況下,很少有人能不再度墮入犯罪圈而成為累犯。如此一來,監獄制度似乎有需要檢討的地方,因為它非但沒有減少犯罪率,反而培養了累犯。這種矛盾的現象,是否應歸因於監獄制度運作不正常,因此需要對監獄制度進行改革呢?從傅柯的的角度看來,並不需要。傅柯認為,人們應該放棄監獄是用來降低犯罪的這種想法,而應認清,監獄的設立本來就是為了要在社會上劃出一個罪犯階級。27 而這個罪犯階級的存在,對於現代權力機制的完美化,有著關鍵地位。
現代權力機制藉由監獄制度創造了累犯圈,並利用其他規訓機構散佈與罪犯有關的論述,用以造成社會全體對罪犯的敵視與恐慌,監獄制度與警察機構遂能在這股強大的敵視與恐慌下獲得存在的藉口:抵禦犯罪。乍看之下,這種狀況相當的詭譎,一方面現代權力機制藉著消除犯罪之名,來取得運用監獄制度、規訓機制與警察機關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這些機構的成立宗旨卻不是為了消除犯罪;事實上,這些機構的成立在於在社會上建立一個犯罪圈,好讓現代權力機制永遠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說,藉由創造出社會公敵,現代權力機制將原本可能遭受的反作用力完全移轉到罪犯身上,並且還使自身得到一個存在的理由,從而化阻力為助力。因此,現代權力機制的技倆,不僅使得社會力量被導離反權力機制的道路,甚至於還使其反過來支援權力機制。我們可以以圖表示這種改良過的現代權力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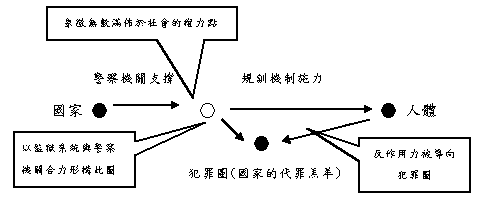
古典權力機制以相當單純的方式來建立起權力場域,它只有兩個端點,一端是君王,一端是臣民,當君王施力於臣民,臣民很自然地反饋一股反作用力回去。前面曾提到,這個施力與反饋的過程並不造成壓迫,而是構成生產。權力能生產論述,權力能製造知識。這種現象也出現在現代權力機制中,只是由於現代權力機制的錯綜複雜,使得權力的生產也花樣百出。譬如說,各權力點對人體進行規訓時,就會因運作的機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論述:學校為了教育而產生關於如何教育孩子的論述;工廠為了有效管理工人而產生管理的論述;醫院則與監獄在犯罪層面上結合起來,分別產生了犯罪心理學、精神病理學與獄政方面的論述;而所有的規訓機構都在製造關於社會公敵的論述,其中以罪犯的論述最為明顯而有效。另一方面,社會在這重重論述的包圍下,所產生的論述並不是像古典權力機制那種反君權論述,反而是被誘導成反罪犯論述,而在無形中成為現代權力機制的支持者。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將現代權力機制與論述的關係以圖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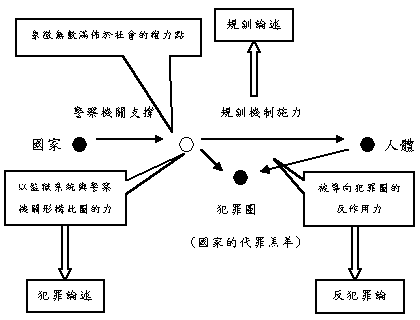
古典時代社會尚可以君權為箭靶,進行抗爭;現代社會則被巧妙而微細的權力機制層層滲透,甚至可以說是被現代權力機制所分化,整個社會分裂成兩部分:罪犯與非罪犯,彼此互相對抗,而讓隱藏在眾多規訓機構後的國家坐收漁利。於是乎在現代權力機制運作下,社會開始被全面的規訓化。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社會相較於古典時代社會,人類不僅未享有更人道的生活,反而更受到權力的全面管束。傳統歷史論述的觀點,由此看來全成了神話。
傅柯接下來所進行的性意識研究,看起來似乎與監獄和規訓無關。但傅柯卻從研究中發現,性意識與罪犯一樣,也成為現代權力機制所極力培養的對象,它們兩者都具有確保現代權力機制存在的功能。因此,本章接下來將以《規訓與懲罰》所建立的現代權力機制架構為基礎,討論傅柯如何將性意識放入這個機制當中及其所產生的作用為何。
《性意識史》是傅柯計畫中六冊性史的第一冊,也是導論。書中雖然曾談到中古甚至希、羅時代的性論述,也旁及女性身體、兒童性行為還有性反常、人口、種族的問題,但這些都只是對未來五冊性史的簡略介紹。28 這本書的主要目標其實是要對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歷史調查,尤其是要研究維多利亞時代 (1837-1907) 以來這一個多世紀的性壓抑 (sexual repression) 問題。29
既然傅柯要研究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問題,那麼什麼是性壓抑呢?按照一般的意見,所謂性壓抑就是「對(性)陳述本身的控制,而且要嚴格地規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在什麼人之間、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上不能談性;也許沒有嚴格到絕對不准談的地步,但要談卻要在一定的範圍內。」30 所以就這個定義來說,性壓抑指的並不是性生理層面的問題,而是指對於與性有關的論述加以限制或規定的現象。但傅柯基於系譜學的設定,對這個定義表示存疑。由於傅柯相信,權力所具有的性質是生產而非壓迫,因此他懷疑:「是否真有性壓抑這個事實存在?」31 為了討論這個問題,傅柯再度訴諸於歷史考察,然而這個考察相當簡略。傅柯只以短短九頁的篇幅來說明性壓抑在中古時代與古典時代的形式,並且強調社會條件不同會造成壓抑方式與內容的不同。然而即便如此,卻已足夠讓傅柯解析出性壓抑的真正性質。
傅柯之所以要將性壓抑回溯到中古時代,是為了要凸顯性壓抑形式中所帶有的弔詭。從中古時期以來的天主教告解儀式中,教士要求信眾能檢查自己的靈魂及感官、檢查自己所有的想法與言行,甚至於反省自己的夢,用以將其中有關肉欲與享樂的內容和盤托出。32 這是一個自我反省的過程,供認自己在肉欲上的非份享樂是為了讓自己戒除這些罪惡,也就是說,為了使自己不再淪入逾矩的性欲滿足中,就必須先將自己越份的性行為說個明白,因此,許多異色的性論述便在這個狀況下生產出來了。這個狀況的弔詭在於,本來是為了減少不合教義的性論述,卻反倒生產了大量這方面的性論述。因此,性壓抑模式並不是不准談,而是要多談那些不准談的東西,好讓人不再談。所以所謂的性壓抑,並不是要完全消除不合規定的性論述,而是要專談那些不合規定的性論述,目的是要讓人知道這些不能談。如此看來,我們可以說,與其說性壓抑具有排除的功能,倒不如說它扮演了生產的功能。
性壓抑所帶有的生產性同樣也在古典時代呈現。在古典時代,原本只局限於宗教層面的告解技術開始擴展到俗世生活上,而此時對性論述的壓抑並不是來自於宗教的考量,而是來自於古典時代重視生產力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性與象徵國力的人口資源與勞力資源相聯繫,將性變成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論述,於是與公共利益無關或違反公共利益的性論述全都受到壓抑。33 然而同樣地,這個看似壓抑的過程其實充滿了生產力,例如政府要求人民不可淫亂,原本旨在使人民回歸家庭生活以生養更多人口,然而卻無形中創造了淫亂的論述;又如學校不准學生談性,卻在發布命令的同時,一次又一次地說出了「性」。如此看來,越是壓抑就越是生產。對傅柯而言,這是再自然也不過的,因為權力的功能原本就是生產而非壓迫,每一次的權力運作,只會生產更多,而不是消滅更多。
性壓抑的模式一旦放到現代權力機制中,就更加明顯。起初人們在治療心智疾病時,認為心智疾病的病因與病人不正常的性生活有關,這種想法發展到佛洛伊德而達致成熟。性壓抑因此乃與醫學甚至精神病理學結合,從知識的角度盡情地對於不正常的性態度與性行為進行研究,甚至於開會討論並且有大量相關書籍上士。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支配下,由財產繼承問題所形成的一夫一妻制,開始從法律層面壓抑與一夫一妻制悖反的性論述。性論述因而牽涉到法律論述,因此,通姦不再只是私德有虧的問題,而是要在法律條文中明定所有違反婚姻的通姦條件與項目,昭於天日,甚至唯恐有人不知。因此在現代,性壓抑的模式以大剌剌的姿態生產著它所要壓抑的性論述,其生產的效能更勝以往。34 然而,這似乎也呼應著現代權力機制的性格,權力的行使更有效,其產能也更大。
從傅柯的討論可以發現,性壓抑其實並不壓抑,相反地,性壓抑專門生產它所要壓抑的論述,從中古時代到現代皆然。傅柯雖然從歷史回顧中將性壓抑的性質梳理明白,但我們要注意,傅柯在《性意識史》中的重點仍放在現代。儘管他的討論範圍上溯到中古時代,然而他藉由中古時代與古典時代來討論性壓抑的篇幅其實只有九頁,因此我們無法將傅柯所寫的這段歷史當成一個獨立的主題來分析,而只能將這簡短的歷史回顧視為傅柯為了討論現代權力機制所作的準備。
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認為現代權力機制的完美化,有賴於犯罪圈的建立。由於犯罪圈的存在,現代權力機制得以能無限行使規訓機制而不受任何威脅。而在《性意識史》中,傅柯也想藉著分析性壓抑,來得出呼應《規訓與懲罰》的結論。從之前的討論可以得知,現代的性壓抑模式主要與醫學論述、精神病理論述以及法律論述連結在一起。而由於性壓抑與醫學的連結,現代性壓抑模式所要譴責的性論述遂與健康有關,它所敵視的性論述具有傷害身體健康的性質,是一種「違背自然」 (unnatural) 的論述,傅柯稱這些「違背自然」的論述與行為為「性反常」 (perverse) 。35 性反常與心智疾病互為因果,兩者脫不了關係;性反常也違反正常的婚姻生活,因為性反常總是尋覓不尋常的享樂方式,如性錯亂、戀物癖、同性戀……。基於維護健康與導正家庭倫理的理由,醫學與法律於是聯合起來,針對性反常提出一系列的治療與懲罰辦法,醫學與法律因此也生產了大量的性反常論述,然而這些論述卻並不僅僅是用來治療與懲罰,而毋寧說是用來為性反常打上記號,並且固定它的位置,叫人不忘記它。也就是說,醫學機構與法律機構在社會上散佈性反常的論述,讓社會大眾對性反常產生警覺與厭惡;甚至使父母、師長、夫妻陷入恐慌,讓他們時時刻刻提防著自己的子女、學生與配偶,深怕後者突然有性反常的行為;同時也使社會大眾不得不更仰賴醫學與法律機構,隨時聆聽著它們所提供的性反常論述。36 然而,無論社會大眾多麼仰賴醫院與法院,這兩個機構其實都無意要消除性反常。它們也許真的對性反常進行治療與懲處,但是它們事實上所作的更在於「論述」的創造,因此,就算沒有具體的性反常存在,抽象的性反常仍舊會持續地縈繞人心,那麼醫院與法院就永遠有存在的價值。準此,性反常獲得了與罪犯相同的地位,它們都被歸類為社會公敵,它們也都是國家的代罪羔羊,同時,他們也是現代權力機制得以完美的兩大功臣。
上節已經提過,《性意識史》的內容完全可以放到《規訓與懲罰》所建立的現代權力機制中來談。因此,這兩本書其實可以一體視之,它們所呈現的歷史形式,都是傅柯一九七0年系譜學成形後所構成的新形式。由於系譜學專門研究權力,也就是論述如何運作的問題,而論述得以運作的力量並不發自論述內部,而是來自論述以外的非論述領域,因此系譜學的研究必須合論述與非論述兩個層面來共同進行,這便解決了之前考古學一直不能克服的問題。
系譜學所構成的歷史形式雖然重新恢復了《古典時代瘋狂史》論述與非論述互動的局面,但並不表示這兩者完全相同。如果從論述與非論述的交互作用來說,系譜學的歷史形式顯然較瘋狂史為細膩,因為系譜學能從力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因此可以補足後者在說明論述與非論述互動時語焉不詳的部份。系譜學所顯示的論述與非論述的互動過程可以以下圖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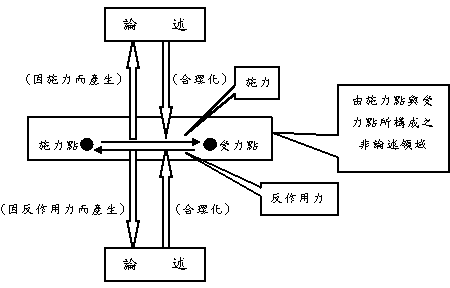
原本瘋狂史只有簡單地談到論述與非論述的互動狀態,但系譜學則能清楚地說明非論述層面內權力的互動關係,並且顯示非論述層面是經由權力關係(不管是施力或是因受力而產生的反作用力)來產生論述;同時,論述則是藉由確認權力關係來進行非論述層面的合理化。簡而言之,論述與非論述之間的互動,仰賴權力關係。權力存在於社會的任意兩點之間,而這兩點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機構,因為有了兩點之間的力的關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才構成了社會各層次的互動,因而才形成歷史。如果說,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向前演進的動力是經濟關係的話,那麼傅柯將會認為,歷史不會向前演進,歷史只是不斷無因果地轉變,而這股變的動力便是權力關係。37 至此,傅柯的歷史研究可以說走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他不僅成功挽救了他自一九六三年以來在歷史形式上沉陷於論述面的困境,還將權力關係置入歷史變動的核心,使歷史內部各層次的互動具有合理的解釋基礎。所以,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滿足了論述與非論述的互動,維持了歷史的整體性;另一方面,也解釋兩層次之所以能互動的原因,可以說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完整而成熟的一部。
然而《規訓與懲罰》也不是沒有缺點。從理論設定來看,傅柯接受尼采將權力定義為抽象的力,以及權力關係就是眾多力的關係的觀點。然而尼采如何能證明世上所有事物之間的關係都屬於「力」的關係?尤其是他認為這些力不可見也無法掌握,只在任意兩點間流竄;如果這些力真不可見,尼采如何得知這些力,又憑什麼認為事物間的關係都是力的關係。尼采顯然作了一個獨斷設定,並且在這個設定之上建立他的理論,因而將事物間的關係約化成「敵對」與「衝突」的對立關係。傅柯在未作合理解釋下就接受了尼采的設定,致使他的研究的理論基礎相當薄弱。
傅柯以權力關係作為歷史解釋的主軸,將現代社會描繪成一個被權力機制完全滲透的地方,將老師、醫生、工廠經營者及社工 (social workers) 視為規訓機制的參與者與操作者,權力機制藉由他們的運作,一波波地在人們身上產生作用,但這些操作者自己也無法自外於這個機制,他們也要接受規訓。因此,生活在現代權力機制中的人們,只有兩種身份:規訓者與被規訓者,而後者是每個人都具有的。38 傅柯的講法實在很難讓人信服,假設現代權力機制真像傅柯所說的那般完美而強大,那麼傅柯本人將只有「規訓」與「被規訓」兩種身份扮演,又何能寫出這本「反規訓」、「反現代權力機制」的作品呢?如果傅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就表示現代權力機制並沒有傅柯所說的那樣完美,它留下不少空隙,讓傅柯扮演一個「反規訓」的角色。傅柯之所以會在著作中呈現一個近乎完美的現代權力機制,似乎肇因於他對歷史資料的運用方式。由於傅柯過度仰賴權力關係來說明現代歷史,所以將整個繁複的歷史場景壓縮成兩個端點間的力量關係;他將歷史資料堆疊起來,用以符應他的權力觀念,因此《規訓與懲罰》所呈現的其時是抽象的權力關係史,這本書寫的是傅柯個人理想中的規訓社會,而非現實的世界。
傅柯在這個時期呈現的作品,在斷裂史觀與連續史觀的爭議上已較為淡泊,傅柯並不傾力於營造一個斷裂的歷史,而是專注於分析現代社會的權力機制。而在對權力機制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傅柯仍一貫地維持他過去所堅持的反進步史觀,這時遂產生一個有趣的效應。由於傅柯不認為人類歷史呈現出越來越人道的進程,因此他的看法明顯屬於反進步觀;但此刻傅柯卻不像過去那樣謹守斷裂的原則:歷史無進步也無退步,歷史只是無因果地轉變而已;傅柯在《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中認為人類「越來越」受規訓,「越來越」受控制,因此如果從傅柯所呈現的歷史趨勢來看,從中古到現代,權力機制「越趨」強大,人則「越趨」渺小,這似乎暗示著傅柯在某些面向上已悖反了他先前的斷裂史觀,而反而有了連續的觀念!
從傅柯在《性意識史》中,針對中古時代、古典時代以及現代所呈現的性壓抑形式而作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每個時代的性壓抑都隨著不同的社會條件而改變,而傅柯在此所設定的社會條件又與《古典時代瘋狂史》相似:中古時代以宗教倫理進行性壓抑、古典時代則以生產力、現代則以醫學和法律來遂行具有繼承權性質的家庭倫理。傅柯因此有重新強調社會條件的傾向,在社會結構的陳述上,隱涵資產階級「逐漸」得勢的現象。如果我們不單憑這一點來證明傅柯已有偏向連續史觀的傾向,那麼傅柯自己也認為(也許是不經意說出來的),中古時代的告解儀式是一種「說」 (telling) 的任務,到了十七世紀,這個任務成為每個人都需負擔的責任。39 也就是說,從中古時代到古典時代,是一個告解技術從宗教界「傳遞」到俗世的過程。而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將構成現代權力機制的兩個要素(規訓與監獄)回溯到古典時代,這兩個要素的擴大與結合,構成了現代權力機制愈趨完美的條件。而傅柯在說明規訓機制與監獄制度的演變時,由於他不再運用結構主義的設定,因此意外呈現出少見的「歷史氣味」,我們會看到一段監獄與規訓的歷史「過程」。而在也許由這些訊息來判定傅柯已接受連續史觀是過於大膽的推論,然而若比較傅柯之前的著作,我們的確可以斷言,在傅柯晚期的作品中,斷裂的氣味少了,而連續的成份反而多了,這也許是因為傅柯不再運用符號學而引致的現象。
綜合以上言之,若不論理論的設定問題,傅柯本期的作品的確更正了論述與非論述不相交流的問題,而在重新恢復論述與非論述交流的同時,又能給予這個交流過程一個更基礎的說明:為什麼會交流?因為力。但是若從理論設定來看,那麼可以說相當缺乏合理解釋,因而呈現出獨斷與輕信的疏忽。而重理論而輕資料的結果,使傅柯本期的作品有玄思的 (speculative) 傾向,因此犯了與他原本用來指責黑格爾、馬克思相同的罪名:目的論;唯一的差別是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指向救贖,而傅柯的歷史則指向完全的被規訓。至於傅柯本其作品中所呈現的連續傾向:越是談體制的越無法避免連續,反之,越是談思想甚至於是談體驗的則越有斷裂的空間。既然傅柯已放棄結構主義的方法,那麼他無論怎麼談體制,都不能拒絕體制中所涵有之堅強內在邏輯,事實證明,他不得不屈服。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回目錄 | 前一篇 | 下一篇